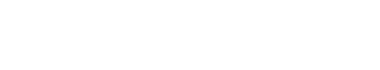浙江大學EMBA吳曉波:學者的本質
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浙江大學“新管理與持續競爭力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主任、浙江大學-劍橋大學“全球化制造與創新管理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睿華創新管理研究所聯席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撥開所有纏繞在浙大教授吳曉波身上的頭銜,他自我評價,“骨子里是個學者。”

過去30年里,這位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的學者,以培養“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的健康力量”為己任,捧著一顆學者心,探究中國企業“之所以然”,參與了一段波瀾壯闊的創新之路。
如今,浙大系崛起為杭州創業的“新四軍”之一,并逐步成為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軍力量之一。作為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核心人物,吳曉波在其間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純粹的快樂
光環等身,角色多重。當記者問到他當下的工作重心時,吳曉波果斷地回答了“教學、科研”。沉浸其中,帶給他純粹的快樂。

他總是很忙。不做院長后稍稍輕松了兩年,最近他又被任命為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上周有一天僅開會就開了四個。他每天也睡得很晚,通常要到一點以后。他當然也想早點休息,可是經年累月,快節奏的生活已變成了他的習慣,變成工作即生活,兩者融在一起了。
在這樣的節奏里,吳曉波始終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學科研上。他的身份認知首先是一名學者、一名老師。無論角色如何變化,他堅持給本科生上了快30年的課,把戰略管理、創新管理的知識傳播給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
吳曉波清楚地了解,年輕人常有一顆不安分的心,“他們總有一些想法在那邊躁動,渴望發生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于是,“過不一般的大學生活”,成了浙大全國首創的“創新與創業管理強化班”每年招新的口號。
每年,60個來自不同的專業的學生,經過兩輪選拔,方得以進入這支浙大系創業“特種部隊”。吳曉波親自為這支部隊教授第一門課,講述最基礎的課-管理學今年,這個班級正好到了第20個年頭,它所培養出的優秀人才里,有杭州的創業明星,也有上市公司的創始人,他們活躍在浙江、全國,更有人把事業拓展到了印度、非洲等海外其他國家。“這體現了我們的精神,叫科技改變世界。”吳曉波有一點自豪。
名聲在外,師德在內。每一年,都有大批人報名,希望成為吳教授的入室弟子。那么,他選擇學生的標準是什么呢?
第一個關鍵詞是有教無類。
“在我眼里,學生各有特點,各有專長,都有潛能,我是一視同仁的。但如果他選了你,你也選了他,那你就用你作為一個教育者的理念和心態去培養他,這個是關鍵。”
第二個關鍵詞是不功利。
“我根本沒有某一種事先的標準,更沒有功利性的標準。不功利,既是我選學生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做人的原則。”吳曉波認為,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消除功利之心非常重要。
最后一個關鍵詞是“上進心”。
吳曉波在選擇學生的時候,偶爾會故意慢下節奏。“有些人跟我說‘選我選我’,哪怕我大致認可他的外在條件,我還是會等一下,看他后面會跟我說些啥,他是用他的功利來打動我,還是用他的上進心。”他說,“有大榮譽也好,小榮譽也好,或者是普通的無名小卒,還是看他是不是有一顆上進的心,他是不是追求夢想、追求變化?有那么一顆不一樣的心就可以。”解釋完自己選學生的理念,他不忘補充道,有些是說不清楚的緣分,有時候也是一念之差。
對于中國管理理論的研究,吳曉波特別強調“頂天立地”的學術理念。頂天,指的是對話國際前沿理論研究,把握學科的動態和前沿問題,用國際化的學術語言詮釋基于中國實踐的管理理論;立地,則要求深入中國管理實踐,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提高管理理論研究的實踐效用。觀其言,察其行,吳曉波正是“頂天立地”這四個字的踐行者。
“如果說我有什么長處的話,就是我愿意很深入地去研究企業。”酷愛實地調研已成了吳曉波的一個特點。凡是去企業調研,他必去三個地點,車間、廁所、倉庫。他認為,調研不只是去董事長或是總經理辦公室里聊天、喝茶,調研需要細致、深入,“你看了這三個地方,才知道這個企業到底管理得好不好。”他不經意地透露自己調研企業的秘訣。
有著共同愛好而惺惺相惜的學者間,有時候也會發生有趣的比試,就如吳曉波和藤本隆宏之間。
東京大學教授藤本隆宏提出了“豐田生產模式”,是日本鼎鼎大名的企業之父。幾年前,吳曉波受藤本隆宏邀請,一同調研了四家日本管理得最好的企業,京瓷、歐姆龍、島津、大金。

吳曉波時任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的院長,他主動對藤本隆宏說,“我做院長太忙了,但我還是堅持去企業,每個月至少會去一個企業。”說完,他等著藤本隆宏的回復。
藤本隆宏淡定地說,“我已經70歲了,我每周會去一個工廠觀察和研究。”
回憶往事,吳曉波向杭商傳媒記者傳遞了他對藤本隆宏這樣的學者的敬意,“這些學者以腳踏實地的態度真正在做研究,他們也影響了我。”他至今記得,藤本隆宏調研企業時,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子。他來到車間里,總是喜歡和工人談話,仔細詢問這個工位的工作情況,盡可能多地將談話內容記下來。而吳曉波也踐行著這樣的研究道路,“我們所要認識及建立的體系,就是既頂著世界的高端和最前沿,又腳踏實地,這樣才能做有意義的研究以促進全社會的發展。”
擁抱創新
2005年,在慶祝SCIENCE創刊125周年之際,該刊向社會各界提出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前沿科學問題,其中一問與社會發展有關。
“為什么一些國家向前發展,而有些國家的發展停滯?”
這個問題的提出背景是,近100年來,最窮的國家與最富的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拉大。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總趕不上發達國家?
近年來,吳曉波的“二次創新”理論在國際上越來越得到認可。事實上,他的理論也為這一SCIENCE之問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如果把國家微縮到企業,向前發展的企業表現如何?
首先,我們不妨用吉利集團的例子,并借用第三方的目光,來管窺一二。
“豐田模式”提出者藤本隆宏與吳曉波的交情始于2003年,當時,他來到杭州,通過網絡渠道,找到了時任吉利集團總裁戰略顧問的吳曉波來了解吉利的信息,并借吳曉波的幫助前往吉利臨海工廠參觀。
參觀完后,回到杭州的藤本隆宏請吳曉波吃飯,兩個人圍繞各自對吉利汽車的看法邊吃邊聊,他頗不以為然地提出了自己對吉利車型的疑問。在國際汽車界領域,小型車的話,兩廂就足夠了。吉利如此簡陋的小型車,為什么要做成大車的“轎車”樣子?
吳曉波說,吉利汽車目前起步條件很差,但是會進步挺快。“根據我的二次創新理論,我們中國企業的創新,往往起步于將引進技術與當地需求的結合,快速地贏得后發優勢。”至于車型,吉利做的是基于中國本土需求的創新。在中國人心里,哪怕是很小的轎車,也得是三廂的。
聽了回答,對于吉利的未來,藤本隆宏搖了搖頭。
2013年,應吳曉波邀請,藤本隆宏出席了于浙大召開的“全球化制造與中國”國際會議,他要求再去吉利汽車看一看。彼時,吉利汽車已經成功收購了沃爾沃、英國錳銅、澳大利亞DSI公司,一時名聲大噪,這中間正好是一個十年。
從寧波工廠回來后,藤本隆宏對吳曉波說,“太不一樣了,你們中國企業學習太快了!”
“吉利用實力徹底改變了藤本隆宏的觀念。他佩服中國企業的學習能力,但認為中國企業在學習中創新的規律,需要被更好地提煉和總結。”吳曉波說,“而我做的工作就是總結提煉我們中國企業從快速追趕到超越追趕的這種規律,又或者說,解讀成功追趕背后‘之所以然’ 。”
那么,吳曉波的“二次理論”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讓我們跟著吳曉波回到1989年。
當時,吳曉波博士生正在杭州齒輪箱廠、杭州制氧機廠這兩家工廠進行蹲點調研。在各約三個月的調研里,他每天跟著工人一起上下班。正是在這兩家工廠的創新實踐中,吳曉波觸到了“二次創新”理論的雛形。
當時國內外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企業創新就是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而這與吳曉波的觀察相悖。吳曉波敏銳地發現,在把國外技術引進來的第一個階段,中國企業并非只是埋頭于消化吸收,而是從一開始就進行大量的創新了,盡管這些創新顯得并不那么起眼。例如杭氧從德國林德公司引進整套技術后,工人們在學習新原理的同時,進行了大量本土化的零部件和流程改進,也就是工藝創新。
結合前人研究及工廠調研,吳曉波有了另一個發現,企業的組織學習模式是沿著產品及技術的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演化而動態變化的,而最關鍵的是在技術生命周期的更新階段所呈現的“混沌”。當時,杭氧已引進并習得了第五代技術,正在努力邁上第六代技術,那么代與代之間是什么關系呢?是再引進還是自主創新?在這個范式的轉變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多的混沌的現象和非線性的變化。這就是越過“追趕陷阱”的關鍵“機會窗口期”。
這時,中國企業是怎么做的呢?杭氧的臺賬清晰地記錄了企業做過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在引進技術之后,杭氧調集來自于不同部門的成員,成立攻關小組,并不滿足于被動的消化吸收,而是更多地以我為主地突破技術瓶頸。
以吳曉波作典型調研的兩個企業為例,他們都通過對引進技術的二次創新,贏得了后發優勢,并成功越過了“范式轉變”期的追趕陷阱,最終實現后來居上。隨著研究企業的數量增多,吳曉波“二次創新”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和完善。他認為,正是中國企業的二次創新,幫助企業贏得了后發優勢。
傳統西方創新理論聚焦一個生命周期內的變化,先是產品創新,接著是工藝創新,然后面臨衰落。然而,吳曉波發現,中國企業實現快速追趕并超越的關鍵是抓住從一個周期更新到下一個周期的“機會窗口”。中國的領先企業在越過周期間的混沌期時,形成了很多特色做法。基于對中國企業特色實踐的總結,吳曉波引申出了很多對管理理論和方法有貢獻的新觀點、新規則,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整套“二次創新”理論。

作為一眾企業的戰略顧問,吳曉波得以把自己的理論應用到企業的實踐中去,使這些企業在科學理性的指導下更好地發展,這當中不乏今日鼎鼎大名者如吉利汽車、海康威視、西子聯合、亨通集團等等,這些企業共同敘述了中國企業二次創新的故事:那就是在引進國外技術之初即快速推進“二次創新”,上臺階后以我為主開展“后二次創新”,再上臺階突破原有技術范式的局限抓住下一個創新范式,實現從追趕到超越追趕的后來居上。
在吳曉波打磨二次創新理論,與中國企業共同成長的這些經歷里,他與華為結緣二十多年的故事不得不說。
1998年,剛從英國劍橋大學訪學歸來的吳曉波受華為邀請,前去講了人力資源與創新管理的課程,雙方就此結識。吳曉波回憶道,那時華為尚處于起步階段,內部的技術能力、管理體系尚且落后。但是,“這個時候它像海綿一樣,拼命在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及資源。”
后來,他還專程赴華為講授了“二次創新”管理體系,在院長任內還去做過華為大學的“引導員”。華為大學是華為培養干部的黃埔軍校,非常特別的是去學習的干部都得自己交學費,還得扣誤工費,華為借此把干部的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在做“引導員”的兩天里,吳曉波對學員進行點評、引導,與之討論。短短兩天的華為大學引導員經歷,讓吳曉波觸動很大,“在這個過程里,我看到一流的企業到底是怎樣奮斗出來的。”
基于相似的價值觀,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與華為特訓營合作籌建了浙江大學睿華創新管理研究所,吳曉波本人及華為國際咨詢委員會顧問田濤擔任聯席所長。
新誕生的研究所由吳曉波命名,名字叫“睿華”。“睿是睿智,華是華為、中華。她蘊含了我們的希望,研究和培養更多優秀的中華企業。”五年下來,睿華秉承著華為和浙大管院共同的價值觀,聚集志同道合者,腳踏實地做研究,在一年四次的“睿華管理四季論壇”中與許多“成長型企業”領導們和眾多華為前任高管們坐而論道,分享華為之道,共同探討企業成長的真諦。
經年累月的交道打下來,華為成了吳曉波近期研究的重心之一。他向杭商傳媒記者總結道,華為的成功遵循的正是二次創新理論所描述的成功之路。在二次創新中實現快速追趕的華為并不甘于享受既得的后發優勢,而是選擇了通過“后二次創新”再往上升級,進而越過范式轉變期以及混沌期,進入“無人區”。在這個階段,吳曉波引入了任正非的“灰度管理”一詞。他指出,在越過范式轉變期、混沌期的時候,適時擺脫“非黑即白”的西方傳統管理理論的束縛,實行“灰度管理”是一種創舉。
“特別是在一些特殊時期,把握事物將呈現的動態性和非線性規律是極其重要的。我干的正是不斷研究規律、傳播規律,然后把它帶給更多的企業的工作。”吳曉波如是闡述他學者的使命。
為了完善自己的理論,吳曉波不僅研究成功的企業,更分析失敗的企業。在這些失敗的企業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正是一味被動的“消化吸收”使得它們不能越過技術范式的轉變期,而掉進追趕的陷阱!這正是對前文SCIENCE之問的解答。
吳曉波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很多失敗的企業,就是因為僅僅滿足于引進、消化吸收,然后進行所謂的再創新。事實上,由于技術發展,當它進行再創新的時候,往往是技術與市場均已換成下一個范式了,此時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再次重復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惡性循環。他指出,唯有那些成功進行二次創新的企業,才能夠越過追趕的陷阱,進而向上躍升。
定義C理論
這是一個在不同場合,反復講述過多次的故事,再聊起來,依然讓人觸動。
80年代初,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吳曉波本科畢業于浙江大學電機工程系,隨后被分配到北京,成為國家林業部的助理工程師,可以說風頭正勁而前途無限。他對這段經歷這樣描述,“哪怕在中央機關里處處得到重視,我心里還是有一些不甘。我并不想看著自己那么年輕就成為一個高高在上坐辦公室的人。提升能力的空間在哪里?”
這個時候,吳曉波遇到了一本書,改變了他的職業生涯。
這本書是商務印書館1983年出版的《來自競爭的繁榮》,它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桔色的封面奪人眼球。其作者路德維希·艾哈德,西德戰后第一任經濟部長,在書中講述了德國怎樣從戰后廢墟里成長起來反超法國。
吳曉波指出了這本書的基本意義——它描述了社會市場經濟是如何在政府正確政策的指引下,激發民眾創新創業的潛力,通過民眾和企業家的行為來改變自己和社會,最終有效分享整個社會的發展成果的。
這本書打動了吳曉波,他直言:“看了這本書,我認為,國家要發展,光靠埋頭苦干的理工、工程、技術還不夠,還要學習管理的知識。”
出生于困難時期的吳曉波,親歷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在國際交流中,他常常跟老外這樣講,“我為自己能夠加入到中國社會巨變的洪流而感到驕傲。”
作為早期經過嚴格篩選而公費留學的學者,吳曉波面臨過一個典型的去留問題。同時期的很多人留在了國外,而吳曉波是個例外。“我是堅定地回來的。”他輕聲說,“我認為,中國還是要靠中國人去改造,去提升。”
吳曉波注意到,很多留在海外的人成了一個旁觀者。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發達社會里享受著各種高福祉,卻又反過來居高臨下地埋怨中國的各種不是。“其實我也討厭社會中許多不好的方面,但總是想著如何盡力去改變。而那些在外面抱怨國內的人卻沒有想過發達國家今天的福祉是怎么得來的。”他停頓了一下,說:“發達國家的福祉不是從天上掉餡餅掉下來的。社會的變革靠的是每一個國民的努力。我們作為受到國家培養而學有所成的人,得以為國家的進步而盡一份努力,這才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是時候了!這些年來,總有一個強烈的聲音在回蕩,推動著吳曉波致力于樹立全新的C理論。他向杭商傳媒記者預告,今年秋季的睿華管理論壇,將專門討論C理論。
C意味著什么?首先,C代表中國,China,它要敘述的是中國企業崛起之道。
吳曉波認為,一個國家的崛起必有與之匹配的管理理論的產生和推動。當工業革命源起英國之時,亞當·斯密塑造了《國富論》,闡述了國民財富的起源,通過“勞動分工理論”指導了英國的崛起;在法國,工程師出身的亨利·法約爾,通過“十四項管理規則”指引了法國企業的發展;德國的崛起有馬克斯·韋伯,他作為官僚組織理論的創始人,提出了官僚組織的六條基本原則;在美國,泰勒、梅奧、馬斯洛、西蒙等人的理論,引導美國成為一代霸主;日本崛起,則有Z理論、“全面質量管理”、“精益生產”、豐田生產模式...凡此等等,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從底層影響了國家的工業文明進程,當今中國之崛起,亟需揭示現代企業管理新規律的“之所以然”之著述。
自建國以來,中國企業起步于被國外封鎖的環境下,整個過程波瀾壯闊,遍布經驗教訓,但結果令人欣喜。經過70年的奮斗,已有一批中國的頭部企業成功崛起為世界一流的企業。
“早在2009年,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的頭號大國,那么中國企業崛起背后的管理理論是什么呢?”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緣起于中國的企業管理理論的缺失讓身為中國學者的吳曉波感到汗顏,“怎么會沒有緣起于中國的管理理論?中國企業的崛起既非完全依賴西方的理論,也不是僅憑借中國的傳統智慧,必然有其背后的中國管理創新!”
吳曉波和他的團隊要提煉一套“C理論”出來,試圖用現代的科學語言去解釋中國的變革及中國企業的成長,這樣才能夠把中國變革的好東西、好規律總結出來,分享并指引更多的企業。
他介紹說,除了China,C理論中含有還有許多C字母打頭的關鍵詞。比如,他用Catch up and beyond來描述追趕與超越追趕,用compromising來描述范式轉變期的灰度;又如,他用complementary來闡述中國企業相互合作互補的特性;而變化change是管理學的重要內容。中國文化對變化的認知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文化對變化往往持有一種更為辯證的觀點,這又是個C;像共創、共建、共享、共贏,是更多的C。

研究常常是孤獨的,也永無止境。
三十年來,吳曉波沉下心來做研究,不斷發現、鞏固和提升自己的科學理論。他說,自己有一個壞毛病,做研究或者寫文章的時候,要有一點背景音。可以是安靜的,可以是熱鬧的,音樂、電影、電視都可以,具體要看心情。
科研工作向吳曉波索取了大量的時間成本,哪怕到今天,他還是得經常熬夜,甚至通宵。有的時候時間流走,但未必轉化成科研成果。在這個過程里,他總是不斷在模糊清晰、模糊清晰,于此過程里進行螺旋式上升。
“我從沒想過不做研究,我感覺到總有一種內心的動力在推動我往前走,因為總能看到社會的發展,看到新的事物、新的形態。新的問題也會被提出來,那我們就不斷去做研究。”吳曉波的聲音平和,語氣平緩。
“如果不做學術,你會做什么?”記者問他。
“哪一天我不做研究了,我就寫小說吧。”這個想法由來已久。他說,在中國社會的大變遷大變革中,這一代人經歷了太多的不尋常,個人的命運、家庭的命運,與整個大社會的變遷是一種怎樣的關系?變革中,多少人跌宕起伏。個人的命運是如此之渺小,社會的變革又如此之宏大,但是最為珍貴的卻是世事流變中的人性光輝。
社會巨變的洪流之中,人生百態的展現、人性的光芒到底會是什么?這些也許會成為未來的“小說家”吳曉波將要探究并示呈于世人的另一類作品。
文/浙江大學EMBA
- 08-10 浙江大學EMBA招生(報考條件/學制學費)信息一覽
- 07-18 浙江大學EMBA三大招生人群
- 09-10 浙江大學EMBA教授張鋼:我們為什么要閱讀經典?
- 08-13 浙江大學EMBA吳曉波:學者的本質
- 03-19 2019年浙江大學EMBA招生錄取第9號通知(筆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