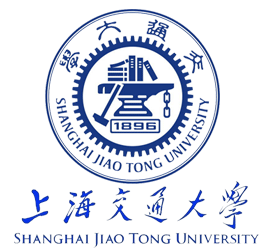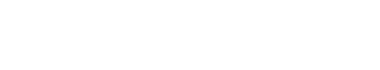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大國大城”的中國思考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EMBA《中國經濟理論與實踐》課程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觀點:“大國大城”的中國思考
時光仿佛倒流,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曾經發生過的城市化模式之辯近年來再次興起。有一種流行的看法,過去30年來大量資源向東部(特別是東部的大城市)集聚,中國的集聚度太高了。那么,中國今天的大城市真的太大了嗎?以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動,控制大城市人口規模,并推進小城鎮建設,讓農民就地進城,就能解決當前出現的種種城市化“問題”嗎?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在其新近出版的新書《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中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陸銘認為,由于受到勞動力難以自由流動的政策限制,中國絕大多數的城市規模是低于其最優水平的。如果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的絕大多數城市應該擴張其規模,而不是小型化。而恰恰是因為對于城市發展規律的認識存在誤區,中國的政策也相應走入了誤區。
人口越往少數地區集中,地區間差距越大嗎?
陸銘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在人口自由流動的過程當中,區域差距一開始是擴大的。因為,此時有一部分勞動者優先享受了發達地區集聚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先富了起來。同時,在欠發達地區還有大量過剩勞動力,即使一部分人口流出,欠發達地區的收入水平也不一定會提高。但是經濟進一步發展,勞動力進一步流動,區域間的人均收入差距會趨向于收斂。
因此,如果政府的政策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特別是限制低技能勞動力的流動,會使區域間差距由擴大轉而縮小的時間點推遲。
結合中國,陸銘指出,長期來看,中國想發揮大國的優勢,就必須實現區域之間人均GDP的趨同,最優的路徑就是國家內部的自由移民。在這個意義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與否的問題,而且是“國家發展戰略”。勞動力自由流動,最終實現地區間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國發展唯一可行的戰略選擇。
大國是不是更需要大城市?
在《大國大城》中,陸銘對大城市的發展機遇做了理性總結,他認為,來到大城市中發展,發展大城市,不僅對個人來說是有益的,對于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的轉型,都是必然選擇。
陸銘以三個D總結了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核心秘密。這三個D分別是Density(密度)、Distance(距離)和Division(分割)。大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顯了規模經濟的優勢,比如分享固定投入、更好的勞動力市場匹配、獲取人力資本外部性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互聯互通水平的提高,經濟和時間距離的縮小會導致生產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取消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割,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三大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其向經濟效率更高的大城市轉移,是提升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所在。同時,經濟的集聚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可以實現在地區和城鄉之間“人均GDP”意義上的平衡發展,從而邁上一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
加快推進小城鎮建設是解決城市化問題的關鍵嗎?
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GDP結構來看,目前54%的城鎮化水平,與工業和服務業已經在GDP中占比90%,并不匹配。國際上公認的事實是,如果按照中國今天已經實現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個百分點左右。
陸銘認為,造成這種結構性扭曲的,是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行政制度。戶籍、土地和社會保障等,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流動門檻,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遠遠落后于由資本積累推動的工業化進程,從而導致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受到限制。
目前中國將加快推進小城鎮建設作為解決城市化問題的關鍵,在陸銘看來,這條路并不可行。通過小城鎮建設,就近城市化,將農村戶籍人口轉變為城市戶籍,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反映的是人口對高收入和高生活質量的追求,城市化對應的是人均GDP的不斷提高。如果僅僅是戶籍身份的轉變,卻沒有對應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和更有效率的GDP產出,或者只有城市面積的擴張,卻沒有足夠的就業增長作為支撐,這種城鎮化建設,不僅是沒有經濟意義的,更會勞民傷財。
大城市該不該驅趕低技能者?
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會想,我們應該更多地歡迎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歡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著應該采取政策去“挑選”勞動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戶本地呢?有些城市出于直覺,認為應該“以業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產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實措施,“清理低端產業”。
陸銘指出,這種想法、做法都不符合經濟規律,一個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務業。對低技能勞動者數量的限制,將減少體力型服務業的勞動供給,其結果就是此類服務價格上漲,進一步的結果是,此類服務的需求相應下降,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的高技能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質量下降。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時,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進入,這不僅妨礙了公民的自由遷徙和居住權,而且也會出現低技能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的怪現象。
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發展的意義何在?
在《大國大城》中,陸銘指出,中國的較發達地區面臨著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權衡。一些發達地區的民眾的思維方式是,外來勞動力來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不行,因為這被認為會攤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如果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區流動,當地政府就需要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需要加大投資,需要更多建設用地指標,需要大量轉移支付,需要借債,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需要用發達地區收來的稅去補貼欠發達地區。此外,由地方政府債務所內生出來的潛在通貨膨脹風險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負擔。因此,發達地區還是要承擔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的代價,只不過這種代價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夠看到。
陸銘指出,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發展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積極作用。即使經濟資源不斷向少數地區集中,只要這一過程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多的就業和收入,其收益能夠超過經濟集聚中伴生的生產要素價格(如地價和房價)上漲等問題,則勞動力仍然會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動。于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減少與戶籍制度相關的社會保障體系分割和公共服務不均等,就能夠促進勞動力流動,釋放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潛力,改變當前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進程的局面。
(文/張帆)
- 11-13 2024年上海交通大學EMBA招生信息解讀
- 10-27 2024年上海交通大學EMBA招生時間
- 08-17 最新上海交通大學EMBA招生簡章已公布!
- 07-28 符合嗎?上海交通大學EMBA招生對象
- 07-25 上海交通大學EMBA招生考試,學歷如何驗證?